这几年,在潮州古城文旅热的催化下,潮州白粥也成为游客争相尝鲜的特色风味。每每路过网红粥铺,都能见到大排长龙等候就餐的“盛况”。
一碗寡淡清素的白粥,诚然难以俘获追寻美食的味蕾。大部分吃货路途迢迢前来吃粥,垂涎的其实是粥铺丰盛的配菜。然而,当吃粥变成一场“宴席”,便体会不到传统潮州白粥的本质了。

白粥少不了杂咸的陪伴。 庄园 摄
中国的粥文化源远流长,而在潮州,吃粥同样有着悠久历史。北宋的吴子野(又名吴复古,号远游,潮州前八贤之一)与好友苏东坡谈论养生之道,就十分推介白粥,说能够推陈出新、利膈益胃。苏东坡一经尝试,果然粥后一觉、妙不可言。
吃粥固然有助于养生,不过,长期吃粥则并不美妙。旧时潮州人热衷吃粥,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。因为地少人多,粮食产量有限,不够吃饭只能吃粥。煮粥往往凭经验调节米和水的比例,于是便会出现一些有趣的情况:水放多了,煮得特别稀,叫“淖饮糜”;水放少了,煮得太过黏稠,叫“洰头抱”。倘若掌握这个规律,则可通过调节粥的稀稠,来控制一段时间的粮食用度。
在经济困难时期,平日吃粥的稀稠度,成了家庭条件优劣的标志。我母亲每当回忆往事,总会说起当年吃粥的情景。家里人口多,兄弟姐妹互相谦让,往往只能吃个半饱,明明很想多添一碗,却再三迟疑,不敢望向饭锅。外公趁韩江涨潮打回来加菜的鱼,餐桌上也事先分配,谁吃鱼头,谁吃鱼尾,谁吃鱼身,谁吃鱼肚,有规有矩不可造次。上门相亲的小伙,谈话间特别强调,他家所吃的粥都黏在饭勺上,要用力敲才会掉下来。可见当时能吃上“洰糜”,是一件十分体面的事。
吃粥是现实所迫,变着法子吃粥,是为了更好解决问题。平凡的白粥中蕴含着从容面对困境的态度和智慧。虽然无可奈何,却不怨天尤人。地不够就精耕,粮不足就巧用,脚踏实地经营好有限资源,创造更大效益来满足生活。这才是传统潮州白粥的本质。
潮州人的生活之道,当然不能只是吃粥。那个年代,设法偶尔吃一顿米饭,是对肠胃最好的调剂。这需要当家人的精打细算。我的外婆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,但只要往米缸里瞧一眼,片刻就能拿捏出当月所剩的用度。倘若“余额”尚且足够对付,便会满足孩子们吃一顿饭的愿望。有时候,多预备一些番薯之类的粗粮,也能节约出吃饭的米来。
对于那个时候的孩子来说,好不容易盼来的一顿饭,简直就是“肯德基”,也就没有平时吃粥那么斯文了。时常听我父亲讲述,头一碗要少添点儿,目的是尽快吃完,好添第二碗。到了第二碗,便毫不客气压实砌高,能装多少是多少……
现在物质生活已经相当丰富,饮食选择应有尽有,潮州人依然离不开白粥。早餐一般都会吃粥,倘若吃夜宵,通常也会选择吃粥。每天从清淡开始,以清淡结束,让肠胃得到良好的调整。
白粥甚至被潮州人视为“良药”。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,经常为了赶稿子错过饭点,加上职场新手精神压力巨大,便与胃痛交上“朋友”。由于我讳疾忌医,祖母便给我煮粥吃。很长一段时间,三餐都是吃粥,不知不觉,我与“朋友”疏远了。我从小到大不爱吃粥,但那段日子,我觉得粥是最适口的食物。
酒场尽兴之后,吃一碗热腾腾的白粥,更是快美无比。就着杂咸,咕噜噜喝上几口,暖和了肠胃,醉意也消除三分。父亲知我长期上夜班,日夜颠倒,经常劝我吃粥“压压火气”。父亲那一代迫不得已吃粥长大的人,非但不厌恶吃粥,更深谙吃粥的益处,这正是潮州白粥的神奇之处吧?
白粥少不了杂咸的陪伴。有人将杂咸说成白粥的“后宫佳丽”,我甚不以为然。所谓“食糜配菜脯”“食糜淋豉油”,形容的是日子过得很拮据。我倒认为,杂咸与白粥是“恩爱夫妻”,相互扶持且主次分明。家常的杂咸种类繁多,如菜脯、酸咸菜、橄榄糁、薄壳米、咸蛋、鱼饭等,大体以咸味为主。潮州人称“买菜”为“买咸”,一小碟“咸”送粥,便足以称托白粥的清香。倘若为吃粥张罗一大桌“咸”,画面就会很奇怪,不符合生活原理。
吃粥自然也可以丰盛一点。如今在潮州的街头巷尾,粥铺随处可见,各式配菜应有尽有。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,光顾粥铺已不是简单只求一饱,而是一种口腹的调节和享受。从行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,吃粥变成“宴席”亦顺理成章。
不过,传统潮州白粥之所以温暖人心,依旧是唇齿间浓浓的烟火气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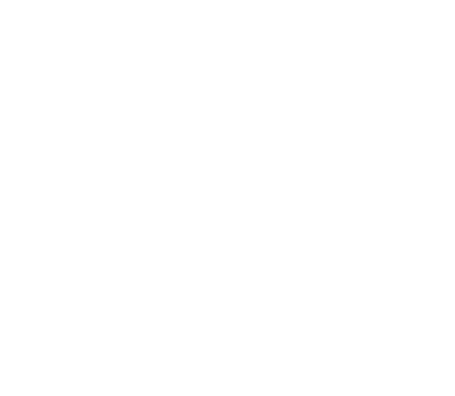
文字|潮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江马铎
编辑|张泽慧
审核|詹树鸿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