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编者按
潮州,这座“活着的古城”,不仅是全世界潮人血脉的根祖地,如今更承载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希望之光。今年,第二十三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将在潮州举行。为了在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上献上一份承载乡愁的精神厚礼,让全球潮人通过笔墨重逢故乡的月光,今天在百花台上推出“烟火抚人心”系列文章。
活动由潮州日报社主办,潮州文学院、潮州市作家协会协办。
文章以潮州民俗文化和非遗代表性项目为主旨和脉络,挖掘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民俗文化印记,通过具象的生活场景、器物细节、节庆仪式等描写,把对家乡文化的深厚情感与独特理解诉诸笔端,展现传统文化如何在平凡生活中抚慰人心,引领成长,滋养心灵。
潮州日报今起陆续择优刊登,敬请垂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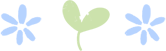

又见朴籽粿
清明,平淡无期的城市,我窝在这个节日里,城市车马稀疏。阴郁,午后,憋出了稀疏的雨。
来自潮汕的快递冷链。有着一股拆谜底的未知,调起了我的精神。
朴籽粿,风尘仆仆赶来了。
箱底静卧的绿意等着我,拆开的第一眼,与它相对照,我热泪盈眶。我看着时间的齿轮,碾过多少个春秋,又是一波翠绿色,呼风唤雨而来,此刻,它让整个清明跳动起来。
风吹草长。这是清明。
清,也是青,树木嫩黄青翠,庵江的水涨了起来。小叶榕树的叶子,又嫩绿地缀在古老的树干上。过年做鼠壳粿的鼠壳可以去田野采摘,就是这朴籽叶没能寻找到。庵埠镇内好像寻不到它的族群。可是每每有翠绿欲滴的叶子连带着整个枝丫,生嫩嫩地来到镇里,来到家汇街上。我们就知道刚刚从树上摘来的,板车上满满的一堆。
“刚刚摘的。”不出所料,戴着斗笠的老者停了车。不像其他买卖,需要高声吆喝,卖者语气淡定,看着如山的绿叶,撒出这么一句。微笑着擦着额头上的汗珠。
已经围了满满当当的邻居。
新鲜的枝头还带着青色的折痕,可以掐出汁液。我一直估算,朴籽树应该离我们街不远,只是长得我们鞭长莫及而已。这是可以卖钱的,它们等不得我们去采摘。问了邻居,果真有去野外摘的,一摘一大捧,需要用绳子捆,像草堆一般,把人都淹没了。
“树很高,你们摘不了。”
推着板车,这一车绿色,卖的倒也不贵。反正我们分好几次买。清明节,卖朴籽叶的人不少,每天都有卖的,就这东西卖得快,一下就剩下板车上的绳子。清明的朴籽粿,要提前好多天未雨绸缪,这绿翠翠的叶子就是赶着这个时候给我们做粿的。挑担卖朴籽叶的也是,一整担子翠嫩的叶子,带着水珠,一下就卖完了。
想想,需要的量比较多,一担子朴籽叶,一户人家就可以包了。
洗干净的朴籽叶铺在竹筛上,放在门口晾干。整条街都铺满了绿色,家家户户的门口都像在争奇斗艳,清明的节气在一街朴籽叶的催促中步履加快了。加快步履的还有家里阁楼那一堆闲置的竹编,这时候它们才得见天日,外婆早已经在溪边洗刷,总有候补替补的竹箕竹篓竹筛,外婆在竹器社工作过,这些竹器完全不在话下。阁楼是个藏宝库,老的旧的没有用的东西都被它收纳,某一天它们都变成非它莫属的某些需要。就像做朴籽粿的那些小陶钵,一个个比碗都小,粗糙简陋,平时没什么用,叠了几堆摇摇欲坠地堆靠在墙边,现在,一叠叠搬将出来,洗洗刷刷,就是要装朴籽粿的,就是等待清明的。
一年用一次,过了清明,它们又将继续呆在阁楼幽暗的角落,又一年的等待。
晾干的朴籽叶,大多还带着小小圆圆的青色果子,用石臼子捣烂。这个过程很是有趣,过年捣糯米绿豆什么,这些都不是我们小孩子能够干的,只有捣朴籽可以,因为捣叶子容易多了,我们能搭上帮手,乐得屁颠屁颠的。
捣烂的叶子汁液特别多,我们用布包起来,挤出汁液,用大陶钵装着。备用。
生米浸泡了捣烂,竹筛子筛了一遍又一遍。南方做粿用米或是糯米,只有朴籽粿一定是米浆原材料。现在把朴籽汁液调好,加红糖,调在米浆里。做朴籽粿不同于梭裸包,红粿桃、鼠壳粿等粿品,所有的粿品都是捏成形,压在粿模里,只有这朴籽粿在经过烈火历练之前是粘糊状的浆。
我们的陶钵有几种造型,桃形、梅花形、星形,还有矮矮的圆锥形。外婆用勺子舀,大鼎里的蒸屉上已经整整齐齐摆满了小陶钵,一个个坐得端正,等着外婆“点将”——舀浆进去。
外婆小心翼翼地给它们添浆。这深绿色的浆液,带着青草的新鲜味道,朴籽叶特有的腥甜味,满屋飘香。这一环节可不能有半点马虎,每个陶钵装的浆液不能太满,六七分,也不能太少,等会涨不起来。这恰好的分寸只有经验老到的外婆可以把控,我母亲都显得生疏了,虽然朴籽粿不用包馅,省却很多时间和劳力。红粿桃和鼠壳粿需要变换咸的、甜的各种不同的馅,朴籽粿却凭着一股纯纯的青绿,完全碾压有馅的粿品。
火候多少?时间多久?外婆也都没有“分钟”或其它方式的计量单位。但绝对恰到好处,这完全是凭着经验感觉。炉灶下的柴火正旺,加柴加风,这是外婆掌控的千军万马,我们使劲地扇,“停”的指令或“差不多”时,我们才能歇息。热气冲着大鼎上的木板盖,顺着它缝缝补补的缝隙蒸腾出来,白烟里泄出朴籽的清香和盖子的木味。
节气已经昭然若揭,清和明,就在木盖子之下。
当木盖掀开时——这便是我母亲也不敢接的活儿,这一掀开,成败在此一举。据说若未熟或过头,皆是前功尽废。未熟者,这一掀开,无法重新回炉。熟过头了的朴籽粿很不好看。
现在灶下的柴火已经抽熄。一鼎白色烟雾散开后,一个个笑意盈盈的朴籽粿如初生婴儿,与我们见面了。
见证这个时刻的还有诸多邻居,沙油佬和别人婶、竹篮婶等,她们家的炉灶也次第生起,这一街邻里此刻更像亲戚,相互照看炉灶并出谋献策。
“笑了——”“笑了——”一众阿婶阿姆发出啧啧的赞叹声。外婆甚是得意,这样的成功自是在一众街坊里隆起极高的声誉。
沙油佬钦点蒸屉里的朴籽粿,竟然“满杯”,没有一个不笑的,一个个都裂开成四瓣,这是最美好的兆头,也是最精妙的巧合,天时地利人和——火候、水(粘稠度)、时间,缺一不可。
炉灶里的火还在继续,紧锣密鼓又开始一鼎蒸屉。每一次做粿,一做上百个都是小意思,又一轮浇筑模具般的打勺,灶里又一次添柴。蒸的次数多了,有时陶钵不够用,需要向邻居借,数数借了多少个?三十还是五十?混搭在一块,反正用完之后,按数量数还给邻居。所以,家里的陶钵经常混淆了其它品种,这些千差万别的陶钵,只有细看才能看出,高低肩或是不规则的圆口,叠起来歪歪斜斜摇摇欲坠。但陶钵这点缺陷并不影响朴籽粿的美貌。
每一个冷却了的绿色造型,都如蚕宝宝般可爱,热气消退它们就可以脱壳了——去掉陶钵。竹篮竹筛就是朴籽粿的存储地。我们的竹篮子多着,分三层,还可增加抽屉。这样存放的朴籽粿透气,很快便失却水分而干硬,这样更容易保存。吃时拿出来蒸一下就恢复原状。
朴籽粿是刚出炉这会最好吃,对比鼠壳粿红粿桃等包了猪肉馅的粿品,它显然素了些。但跟清明这个节气刚好配搭。
在广府,我瞧见梅花状模样的它,自是欣喜异常,指着这翠绿的朴籽粿问:这是什么做的?
“艾叶。”
我失望至极。朴籽粿怎么是艾叶做的呢?
“那你们是用什么做的?”
我比划半天,竟然无法让人家明白“朴籽”究竟是什么植物!我纳闷,粤北和珠三角的植物丰茂,应该有它的植株,只是除了我们潮汕给予“朴籽”的名称,是不是其他地方它应该是不一样的名字?
只有潮汕的“绿叶团子”,才用朴籽叶做,其它地方再无雷同。
寻寻觅觅多年愣是找不到朴籽树的踪影,抑或见到而不识庐山真面目,它究竟像什么树呢?极其普通的叶子,真像家汇街上那棵老槐树的叶子,连果子都像。
这地域特征明显的朴籽粿啊,让潮汕的孩子也循着那味儿。
“糟了,我发现我越来越像你,也喜欢朴籽粿。”女儿抢了快递里几个朴籽粿打包而去。潮汕的东西,就像故土的召唤,离得越远,越能在喧嚣声里破土而出。
清明,与思念有关,与游子有关,扫墓,祭奠,清明在很多人心里,比春节更重要。
车辆驶出城市,奔向每个人的故土,清明的城市,空荡荡的,应时而落的雨水,更多的水分和思念,还憋在云层中,写满整个天空。
时节,是上苍给我们漫长的人生掐入的一个个驿站,清明,在这里停息,让我们与祖先握手,与来自土地的植物深吻,与我们的根叙旧,然后整装待发,再继续我们的人生。
文字|鄞珊
编辑|翁纯
审核|庞磊成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