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场戏外戏
□ 李英群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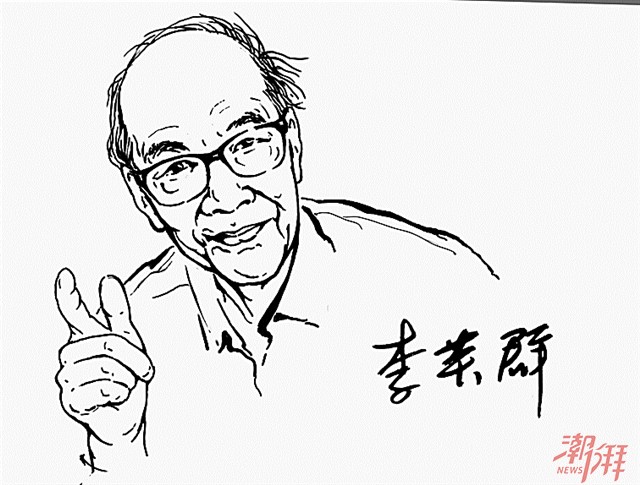
戏剧演出一般有两种场所:一种在封闭的空间,即戏园和会堂馆所中;一种在开放的空间,即在广场或田野中,临时搭的戏台上,后者被称为广场戏。
论观众面和影响力,戏园戏远不及广场戏。
时下,某乡某村,请剧团到来演出三几个晚上,是很平常的事,但在我的童年,乡里做大戏,那绝对是百年盛会。
忆起我12岁那年,乡里做大戏的轰动,历历如在眼前。
秋收过后,过年前夕,村里传出乡里的老大,即有威望的长辈乡亲正醒酿着在正月头请班大戏来乡里演出的事。消息不胫而走,一股兴奋的气息在村里弥漫。
终于好事成真,请的戏班和演出日期都定了。全村人沉浸在兴奋之中。大戏未上演,戏外戏却登场了:女人们开始走亲戚了,邀请“四亲二情”,三姑六妗到时来看戏!
乡里做大戏,绝对是可以写入乡志的历史性事件,是全乡人最有脸面的喜事,谁家的亲戚来得多,就是脸上有光。于是,大戏演出前,乡里都是光鲜亮丽的走亲女人,家家都与亲戚欢聚,这一出戏外戏,可名之为《走亲盛会》,会持续到做大戏后三几天。
第二出戏外戏是《小孩狂欢》。真有点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味道,消息刚在酝酿,儿童们就当作真消息飞快地传出去。我承认自己是个最热心传播者。那时,我常在闲间当茶童,从大人们的议论中得到消息,兴奋得不得了。我是在小伙伴们中唯一看过大戏的人,被大戏的非凡魅力震慑过。那是10岁那年到浮洋一亲戚家做客时跟大人到戏园去看过,坐在第四排台上的刺眼灯光,艳丽服饰,生旦丑净,唱做念打都令我终生难忘。今日乡里要做这种大戏,简直难以置信。于是一点一滴的新讯息,我都及时告诉小伙伴,在乡里传开去。
每天都与小伙伴聚会交流消息,去准备搭戏台的大宗祠前广场上考察。
终于,住在大宗祠边的伙伴來告知搭戏台的来了,急急飞奔而去。只见广场最远处小河边上堆满杉木竹竿竹篷和一大包一大包的篷布,有十几个壮汉在忙着,真不知他们怎么把这些大家伙搬来,尤其是不少高脚凳子。围观者不单有我们一众儿童,还有不少大人。看搭台人手脚麻利,动作熟练,分工明确,进展神速,真佩服!
看得很投入,日已过午,不回去吃午饭要挨母亲骂,匆忙回家。饭已冷了,不管,狼吞虎咽。母亲说我这几天像无头苍蝇,忙飞乱闯。要我去山脚菜园割菜。还是父亲理解我,说千古世年做次戏,小孩要玩就去玩,割菜由他去。
跑到大宗祠广场,继续欣赏搭戏台,直到黄昏回家吃晚饭,就不敢再去了。第二天再去,戏台已搭好。好家伙,真高真大啊,那个做戏的平台,就有一个成年人身高!
次日睡得沉,母亲也不叫醒我,直到家住枫江渡口的伙伴来告知:戏班的船到码头了,戏仔正在上岸。这可是我们最为期盼的场面,要近距离看看我们的同龄苦命人。于是饭也不吃了,狂奔而去。可惜,被告知戏仔们已入住乡里的中心小学了,外人不让进出了。只好听那几位见到戏仔者兴奋的转述。
戏正式演出时,是没有我们观赏的份的。戏棚前真正是人山人海,最佳位置是男子汉的天下,外围是站在椅上桌子上的姿娘们。我们只好分散着找高处,终于爬上远处人家的屋顶去,远远地,也算看到全舞台的活动。正有点开心之际,被主人发现,坚决地赶了下来,说你们若掉下来他们担当不起。
再另找地方吧。广场边那大榕树上能看到戏台的地方已被另外的小朋友占领了。这下真的成了无头苍蝇乱飞乱闯了。跑到戏台右后侧听戏仔们齐齐的帮声,到戏棚下听演员的脚步声,听台前不同村落来的后生兄为占好位置的角力,互相挤压的喘气声。终于到了午夜,分别被家长找到,带回家去。我父亲带我回家时,不忘买一串“鸟来脯”作安慰。
第三出戏外戏,我名之为《棚前青春秀》。观众席外围,摆了高矮不等的椅子,桌子,包括小学那张乒乓床。演戏时,那是村里姑娘们的站位。她们平时从不化妆,今晚都略施粉黛盛装出场,展现了她们的青春美。这是媒婆们最关注的目标,也是某位暗恋后生兄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的那人。演出前半场,台前最佳位置则在进行一阵阵角力。迟到的后生兄从戏棚下合力往观众座挤,已占了这位置的后生兄全力顶住,一波波的你来我往,总是转移看戏人的注意力。镇住了位置者与被挤到外围者过后有一阵子安定,双方表现友好,不久,失败者又想法挤回来,或者又有迟来观众照前例从台下向观众座冲挤,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表演,绝不会伤害对方。目的主要是表现青春活力,不无表演给姑娘们看的意图。就像当下的摔跤比赛,过后双方友好握手。
过后,在闲间,我会听到大人们在津津乐道当晚是某村青年表现最佳,甚至开玩笑说择女婿可到该村。
多年以后,我听到那首《阿里山的姑娘》,回忆童年乡里做戏的棚前青春秀,不禁改其唱词,来了这么二句:
戏棚前的姑娘美如水呀,
戏棚前的少年壮如山!
随着乡下演大戏的不再稀罕,旧时这种戏外戏也随着时代远去。新时代应该有新的戏外戏。
编辑|张泽慧
审核|詹树鸿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