呾有呾无
李英群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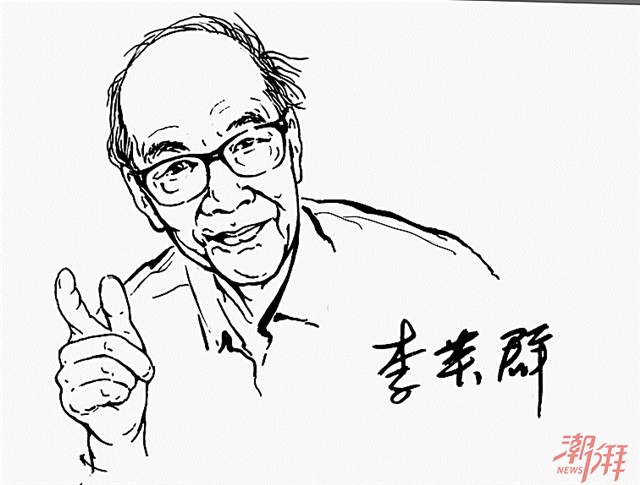
呾有呾无,是潮州方言口语,常指昔时闲间茶座的聊天,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些不痛不痒的琐事。这是我童年在乡下闲间当茶童时所见的常态。
一直认为这有与无,就是生活中那些最无所谓的事物。乡亲们作为话题,无非打发时光,至于为什么闲聊不叫谈天说地而称为呾有呾无,并不放在心上。
关于有与无,年轻时还因为其读音而引起很大兴趣。“有”,潮州话读音与普通话的“无”字读音,完全一样,觉得很好玩,以为一个北方人如果来到潮州,知道无就是有,可能会觉得左就是右,在马路上乱闯。这自然是小孩子的认识,长大了点就不再这么天真了,但却迎来一个更大的命题:有与无的关系。
读了一些书,知道“无”与“有”的关系,居然在中外哲学传统中有着极丰富的思想体系,根本不是我们乡下闲间所讲的有有无无,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就提出“天下万物生于有,有生于无”的论断;西哲黑格尔则论证了“纯有”与“无”的辩证转化。这么高深的论述把我这个从乡下闲间走出来的野小子吓坏了,我立即辞别他们,回到潮州乡亲中品味我们的文化。
但毕竟摆脱不了老子们的影响。当我正在探索为何潮人要把“有”的读音念成与普通话“无”一样无二呢,就忘不了老子“有生于无”的影响。脑中牢记着成语“无中生有”。我当然认为是我们潮人很“老土”,有与无是事物的两端,意思完全相反,你居然不回避,以有当无,将无作有,真个乱了套!
然而,当我被定性为一名文化人,并且在退休之后潜心研究潮州文化尤其是方言俗语之后,我发现我错了。潮人不单不老土,而是特精深,就这个把“有”读作WU可证。
我们潮人祖先从中原南迁,在那把“无”字读WU的地方来,到南海边定居,把“有”读为WU,绝非误读,更非不懂,更大可能是有意为之!因为他们都是满腹诗书的当地望族,知道“无生于有”,无就是有,在这省尾国角,自成一统,自开一枝。这里山高皇帝远,环境更为宽松,他们的幽默、诙谐天性得到表现,创造了许多生动,活泼的方言辞汇,其中不乏风趣,古怪的用词一点也不奇怪,更因为“无就是有”的现象,在日常生活中,在文学艺术领域极常见,在说有,却从无说起:
无耻,斥一个人无耻,他必有耻,耻得自己不知廉耻,就是无耻;无事不登三宝殿,就是有事;无边无际,就是广阔的存在,是大有。
在艺术作品中,音乐的休止符,文章的省略号,山水画的留白,戏剧表演的哑场,都是“无”,也都是“大有”。
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有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句。我读到“曲终收拨当心画,四弦一声如裂帛,东船西舫悄无声,唯见江心秋月白”时,心中一阵发紧,在无声的状态下,耳畔是她的整首曲的轰鸣,那最震撼的旋律久久回荡,深深感到此时无声胜有声。无非无,乃大有。
写文章的省略号,把内容省去,当然是一种无,谁都知,那里面藏着更多的有,让读者自己去填补。无非无, 乃大有,正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也。
中国山水画的留白,更是无中生有的最经典范例。
我读画不多,记得看过一幅古代山水,画面是一叶扁舟,一位渔翁,很小,其余95%是空白,感觉是无限浩渺的江天,显示渔翁绝对的孤独。问一位画家朋友,知是宋代马远的名作《寒江独钓图》;我用心品赏的山水画是元代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,还专门跑到富春江,从富阳到桐庐河段考察一个来回,画作与自然各有千秋,而画作中许多留白的确为画作增色不少。因为那些留白就似烟雾,罩住青山绿树流泉村舍,而且仿佛有流动感,顿使画面气韵生动。
这二幅画的留白很出名,被后人称为“马远的天空、黄公望的烟岚”。
我终于打心眼里佩服潮人先辈故意把“有”的音读为普通话“无”的可敬和可爱,这是最能展现“有生于元,无中生有”的哲学观点的最通俗也可最被常用的创意。
也许,我这呾有呾无是在白食白呾,权当茶余一乐!
编辑|张泽慧
审核|詹树鸿











